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白血病淋巴瘤学术
年7月13日,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白血病·淋巴瘤学术会议在哈尔滨正式召开。本次会议由中华医学会、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主办,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、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、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、医院血研所和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协办。
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王建祥教授,医院、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黄晓军教授,上海交通大医院沈志祥教授担任大会主席,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马军教授、医院吴德沛教授担任执行主席。
学术报告撷英
王振义院士通过分享临床病例,介绍了近年来先发现的“慢性粒单白血病伴发母细胞样树突状细胞瘤”这一疾病。以病例作为引子,王院士提出以下问题:
围绕母细胞样树突状细胞瘤(BPDCN)的本质、细胞来源、诊断标准,王院士明确了病例中的患者符合BPDCN诊断。同时,依据慢性粒单白血病(CMML)的诊断依据,病例中的患者符合CMML诊断。
这两种疾病可以同时发生?同时发生背后的原因何在?针对这些问题,王院士对近几年领域内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分析,并发现,BPDCN与CMML存在同源、同期突变,这为两种疾病的并发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。而如何进一步明确其中的机制、明确诊段标准及诊断流程、摸索出疾病的最适治疗方式,仍需要继续探索。
王院士指出,医学的本质就是不断迎接新的挑战,而以科学的态度、从发病机制到临床诊疗逐步探索,也正是医学发展的方向。
黄晓军教授以“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——中国的视野看全球”为题,从“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现状、疗效及单倍型供者是最佳替代供者”3个角度,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。
黄教授首先通过流行病学数据指出,白血病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,而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白血病的有效治疗方法。然而,供者缺乏限制了其应用。为解决这一问题,突破单倍型移植“禁区”,黄教授及其团队在通过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(G-CSF)联合胸腺球蛋白诱导免疫耐受的基础上,建立了国际原创的、非体外去除T此包单倍型相合骨髓和外周血混合移植体系(这一方案也被国际学者称为“北京方案”,方案发展详见下图)。
这一方案有以下创新点:①结合多种生物标记物,创建适应不同状态、年龄的个性化单倍型移植新方案;②突破组织配型对供着选择限制,阐明影响单倍型移植疗效的供者特征,挑战造血干细胞移植60年经典规则;③优化单倍型相合移植后真菌及EB病毒感染防治方案。
过去10余年中,该方案取得了与人类白细胞抗原(HLA)相合同胞供者移植和HLA相合无关供者移植相当的疗效。在治疗儿童恶性血液病方面,该方案疗效优于脐血移植;在治疗中、高危急性髓细胞白血病(AML)和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(ALL)方面,该方案疗效优于单纯化疗。
方案的单倍型关键技术获得了国际学术权威专家的赞誉,也在国际和国内广泛推广应用。在我国,单倍型移植称为第一位的移植模式,在全球应用中,与国内外同类技术体系相比,亦处于领先地位。
黄教授指出,“北京方案关键技术应用改变了全球造血干细胞移植格局,使得几乎所有白血病均可通过移植获得治愈。”
美国纪念SloanKettering肿瘤中心白血病病病房主任、Blood杂志副主编MartinS.Tallman教授,介绍了目前AML和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(APL)领域内的最新进展。
Tallman教授首先回顾了从年至今AML临床实践中的几次变革(下图),并总结近来对AML的最新认识包括:①AML的细胞遗传学特征及分子相互作用;②强化诱导/低强度维持方案;③微小残留病(minimalresidualdisease)的重要性不断凸显;④同种异基因移植适应证不断扩展;⑤老年患者获得更多治疗机会;⑥新药及新药及现行治疗的联合治疗充满希望。
对于APL,Tallman教授指出年最重要的问题包括:①如何减低早期死亡率?②ATRA/ATO是标准的治疗吗?③对于高危患者的最佳治疗是什么?④需要维持治疗吗?同时,Tallman教授也分享了对APL治疗的想法:
1.早期死亡是治疗失败,不是耐药;
2.典型的预后因素并不重要(FTL3、二重APL);
3.目前的治疗是减少化疗药物,并且无化疗也可治愈APL;
4.老年患者与年轻患者具有相同的治疗敏感性;
5.复发后治疗也有效;
6.自体移植是CR2的治疗选择,而不是异基因移植。
综上,减低早期死亡率、优化高危患者的治疗策略是未来方向。
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OwenAnthonyO‘Connor教授,以“淋巴瘤治疗新药,将会发生什么”为题,展望了淋巴瘤治疗的未来。
在演讲伊始,Connor教授提出问题——淋巴瘤医疗新药,正向着“无化疗”的未来前进?围绕这一问题,Connor教授逐一介绍:①并非所有的PI3K抑制剂都一样,事实上,这类药物之间存在差异;②来自新型混合融合技术的分子(ESO-S-);③靶向核蛋白代谢药物(Selinexor);④将强效药物与单克隆抗体偶联(抗体药物偶联剂和CD37);⑤吞噬或不被吞噬(靶向于CD47上SIRPαFC的药物)这些药物的原理及相关研究。
在演讲最后,对于“淋巴瘤医疗新药,正向着‘无化疗’的未来前进?”这一问题,Connor教授给出了自己的回答:
1.抗肿瘤治疗进展明显,目前强调于靶向肿瘤的生物特异性治疗和免疫治疗;
2.新型细胞毒药物-EDO-S,被独特的抗肿瘤药理和传统细胞毒机制原理所改变;
3.并非所有的同类药物都相同(如化学作用、细节等),更重要的是明确为什么会存在差异;
4.免疫治疗不仅仅是一种单抗治疗,目前仍存在更多的可能;
5.新药联合以及新药与传统药物的联合可能带来疗效的提高,但未来的开发速度可能受限。
医院朱军教授分享了“北肿单中心淋巴瘤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实践与思考”。
围绕:①在新药的时代淋巴瘤ASCT的地位如何?②在中国淋巴瘤的ASCT做的够吗?③淋巴瘤ASCT适应证如何选择?④与处理方案比较?⑤如何减少ASCT后的复发?5个问题,朱军教授逐一介绍了北肿淋巴瘤ASCT在各病理亚型中的成果,并总结:
1.ASCT具有很好的安全性可显著提高长期生存;
2.免疫化疗时代,ASCT治疗淋巴瘤仍具有重要地位;
3.ASCT的价值在各病理亚型中均得到体现;
4.关键在于选择ASCT的时机;
5.需要把控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适应症;
6.尝试减少ASCT后复发的方法与途径;
7.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ednhc.com/wazlyy/10008.html
- 没有推荐文章
- 没有热点文章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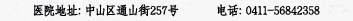
当前时间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