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同病理分型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CT表现分
作者:赵曦曈岳松伟程强刘佩常丽阳赵晓晓梁盼
来源:中华医学杂志,,97(01):43-46.
摘要
目的
探讨不同病理分型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(IMT)的CT表现,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及诊断水平。
方法
回顾性分析年2月至年11月医院29例经病理证实的IMT的临床和影像资料,并结合文献资料分析总结该病的CT表现特征与病理基础,并对3种病理分型的IMT患者性别、肿瘤形态、肿瘤边界及位置(肿瘤位于头颈、胸部、腹部),分别进行χ2检验。
结果
29例患者年龄2~78岁。黏液血管型7例,梭形细胞紧密型13例,纤维型9例。免疫组化:Vimentin(22/29),SMA(28/29)为强阳性表达,ALK(4/29)及CD-67(6/29)为部分表达,其他标志物S-等为阴性表达。χ2检验显示仅有患者的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(P0.05)。
结论
不同病理分型IMT的CT表现及临床特征存在差异,但最终确诊仍需结合病理及免疫组化。CT检查对明确病灶范围以及与邻近结构关系有重要价值,可以指导临床选择合理的治疗方案。
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(inflammatorymyofibrob-lastictumor,IMT)是一种少见的具有恶性潜能的间叶源性肿瘤,归类为纤维母细胞/肌纤维母细胞肿瘤、中间性,少数可转移,具有局部侵袭、复发甚至远处转移等恶性肿瘤的生物学潜能[1],但影像学上无明显特异性表现,容易误诊。IMT的治疗与它的位置及其组织学分型有一定的关系,如肿瘤容易切除,以手术治疗为主;而药物治疗可以应用在手术不能切除的情况中,根据其不同组织学类型,进行药物治疗的方法也有所不同[2],故对不同病理分型IMT的CT表现的探讨显得尤为重要,并且以往对不同病理分型IMT的CT表现的文献较少。本研究回顾分析年2月至年11月医院经病理证实的29例IMT患者资料,观察并总结CT表现,旨在探讨不同病理分型IMT的CT表现,提高对本病的认识,以指导临床。
1对象与方法1.患者:
29例IMT住院患者,其中男14例、女15例,年龄2~78岁,中位年龄39.5岁。头颈部肿瘤5例,胸部5例,泌尿系6例,腹膜后4例,盆腔3例,肠系膜5例,阴囊1例。
注:患者的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,P=0..检查方法:行常规64排平扫加增强检查,具体扫描参数:管电压kV,管电流~mA,层厚5mm,重建层厚1mm。增强扫描经肘静脉以2.5~4.0ml/s注射非离子型对比剂(碘含量g/L),总剂量按1.5ml/kg计算。注射对比剂后25~30s行动脉期扫描,60s行静脉期扫描,s后行延迟期扫描(具体时间根据患者的心功能情况而定)。
3.病理学检查:
病理图片由同一位病理科医师阅片。采用组织切片HE染色镜下观察,鉴别困难者行免疫组化染色,主要包括波形蛋白(Vimentin)、平滑肌源性抗体(SMA)、ALK、CD-67、S-等;根据Coffin等[3]提出的3种组织学类型为标准来进行分组:(1)以黏液、血管及炎症细胞为主的黏液血管型为一组;(2)以梭形细胞为主,混杂有炎性细胞的梭形细胞密集型为一组;(3)以致密胶原纤维为主的纤维型为一组。
4.图像分析:
所有数据传至GEADW4.6工作站进行MPR重建冠矢状位,重建层厚3mm,层间距3mm,以便显示病变与周围组织关系。由2名具有10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放射科医生独立阅片,分别记录肿瘤发生部分、大小、形态、密度及强化特点等。在横断面肿瘤最大径显示层面上,测量瘤体大小采用横径×前后径。增强后CT值增加0~20HU为轻度强化,20~40HU为中度强化,40HU以上为明显强化。
5.统计学方法:
采用SPSS21.0统计软件,分类资料计算频数及百分比,采用χ2检验,以P0.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。
2结果1.患者临床资料及CT表现:
3种病理分型的IMT患者性别、肿瘤密度、肿瘤形态及边界分别进行χ2检验,其中肿瘤形态及边界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(均P0.05);而患者的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(P=0.),其中黏液血管型以女性多见,梭形细胞紧密型男女分布相似,而纤维型则以男性多见(表1)。
表1
29例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患者临床资料及CT表现与病理对照表2.不同病理类型IMT发病部位及与周围结构关系:
本组IMT发生在头颈部5例,胸部5例,泌尿系6例,腹膜后4例,盆腔3例,肠系膜5例,阴囊1例。其中28例为单发,1例为多发。对3种病理分型的IMT患者肿瘤位置(肿瘤位于头颈、胸部、腹部),进行χ2检验发现,其发病部位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(均P0.05)。(1)黏液血管型:6例为单发,1例为多发(图1A,图1B,图1C,图1D)。发生在喉部1例,腹膜后1例,膀胱2例,盆腔2例,结肠1例。盆腔1例累及子宫、附件及直肠壁,直肠壁增厚;盆腔1例与膀胱、子宫分界不清;腹膜后1例可见腹盆腔大量积液,伴双肺转移;1例喉部病变内可见钙化灶。(2)梭形细胞紧密型:均为单发。发生在喉部1例,甲状腺1例,颌面部1例,肺部3例,腹膜后2例,回肠1例,肾脏2例,膀胱2例。甲状腺1例病变压迫气管,颌面部1例病变造成右下颌局部骨质破坏,肾脏1例侵犯肾皮质,腹膜后1例病变上缘与左肾下极分解不清,左肾受压上移;喉部、肺部(图2A,图2B,图2C)及纵隔内各有1例病变内可见钙化灶。(3)纤维型:均为单发。发生在鼻窦1例,胸壁1例,肺部2例,盆腔1例,肠系膜3例,阴囊1例。胸壁1例造成第2肋骨骨质破坏,盆腔1例(图3A,图3B,图3C)累及左侧闭孔内肌、臀大肌及左臀部软组织,其内可见左侧髂内动脉末段、髂外侧动脉、闭孔动脉、臀下动脉穿行,并伴有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肿大。
3.病理及免疫组化结果:
大体病理:肿物切面呈灰红色或灰白色,质地较韧,周围可见纤维包膜。镜下:肿瘤细胞由梭形细胞构成,排列成束状、树状、编织状或席纹状,核居中呈卵圆形,其中可见不同程度胶原化及黏液水肿,以浆细胞、淋巴细胞、嗜酸性粒细胞等炎性细胞浸润为背景。其中以血管较丰富为主要特征的黏液血管型7例(图1D,图1E,图1F),以梭形细胞密集为主要特征的梭形细胞紧密型13例(图2D),以胶原密集为主要特征的纤维型9例(图3D)。免疫组织化学:Vimentin(22/29),SMA(28/29)均为强阳性表达,ALK(4/29)及CD-67(6/29)为部分表达,其他标志物S-等为阴性表达。
3讨论1.IMT的临床及病理特征:
IMT是一种少见的间叶源性肿瘤,可能是人体对损伤的一种异常或过度的反应。免疫组化证实梭形细胞表达间叶细胞标记Vim和肌源性标记SMA、MSA,Vimtin通常强阳性,SMA、MSA反应为局灶性或弥漫性[4]。ALK在儿童和青少年时常为阳性,而在成年多为阴性[5]。本组研究结果显示,Vementin(22/29)、SMA(28/29)为强阳性表达,ALK(4/29)及CD-67(6/29)为部分表达,其他标志物S-等为阴性表达。3种不同病理分型IMT患者间性别分布存在差异,黏液血管型患者以女性多见,梭形细胞紧密型男女分布比例大致相仿,而纤维型患者以男性多见。最好发于肺,其次为肠系膜、网膜和腹膜后[6]。临床表现为良性,但随着病程迁延,可有局部复发或转移[7]。以腹部和鼻窦较易复发,伴局部浸润表现[8],可能与ALK阴性有关[9]。
2.IMT的CT表现及病理基础:
该病病理组织学包含纤维组织增生、炎性细胞浸润、凝固性坏死以及炎性反应[7]。本研究通过对29例全身各部位IMT的CT表现和病理学进行对照分析,总结出以下特点:(1)肿瘤形态、大小及边界:一例为多发肿块,呈类圆形或不规则分叶状,其边界较清。本组肿瘤横径从1.3~11.4cm,以腹腔、腹膜后、盆腔及纵隔肿瘤体积较大,发生于头颈及空腔脏器的肿瘤体积较小,可能与其部位间隙大小及症状出现的时间有关[7]。(2)肿瘤密度、强化方式及病理学基础:肿瘤可为囊实性混杂密度,可有钙化,与病变成分有关[10]。黏液血管型:实性成分呈明显花环样强化,静脉期强化进一步增高,可能是由实性成分镜下伴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增生,间质内大量炎性细胞弥漫浸润,导致肿块内血管管壁通透性增加所致[8]。囊性低密度无强化区镜下为黏液样变形、炎性渗出或坏死。梭形细胞密集型:增强扫描呈渐进性延迟强化特点,但强化程度弱于黏液血管型。分析与其实性成分镜下为增生的梭形细胞紧密排列有关,肿瘤细胞紧密排列,对比剂廓清较缓慢,故其增强后呈延迟强化特点。纤维型:增强扫描实性成分强化不明显或呈轻中度强化,分析与其实性成分镜下肿瘤细胞稀少,以胶原纤维为主,故其增强后强化不明显或呈轻中度强化。本组梭形细胞型和纤维型以实性居多,仅有2例表现为囊变坏死,可能与其肿瘤体积较大,病程较长有关。本组病例中有部分黏液血管型、梭形细胞紧密型及纤维型之间强化方式相似,可能与其病理成分、细胞排列及对比剂扩充时间有关,此类病例仅靠CT表现难以鉴别。本组29例术前CT均误诊,其中23例诊断为良性,6例诊断为恶性。发生于肺部的IMT需与肺癌及肺部其他良性肿瘤鉴别;发生于腹腔的IMT需与胃肠道间质瘤鉴别;发生于腹膜后的IMT需与淋巴瘤、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、各种肉瘤等鉴别;发生于软组织内的IMT需与神经纤维瘤或神经鞘瘤等鉴别。
综上所述,不同病理类型IMT患者的性别分布具有差异,女性患者多考虑黏液血管型IMT,男性患者以纤维型IMT常见。黏液血管型IMT的CT增强表现较具典型特征,结合CT和临床表现可初步诊断。梭形细胞紧密型、纤维型CT及临床表现特征不典型,术前诊断困难,确诊仍需依赖病理。CT对明确病灶范围以及与临近组织器官关系有重要价值,对指导临床选择合理的治疗方案有重要价值。
赞赏
长按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ednhc.com/ways/11831.html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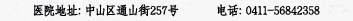
当前时间:
